原载《晨报星期画报》1927年 第2卷 第85期
林风眠
我们一谈到了解艺术这句话,就从很简单的问题,谈到很复杂的问题上来了。但是我们研究艺术的人,应当首先决定我们的态度,我们从事艺术上之创造,究竟是为艺术的还是为社会的呢?从前欧洲的学者在艺术上争论之点,总离不了“艺术的艺术”和“社会的艺术”两方面,极端争执,视为无法调和,而变成两不相容之态度,其实这种过于理论的论调,愈讨论愈复杂,如同讨论美的问题,竟谈到上帝上面去了。
托尔斯泰的《什么是艺术》书中,谓“艺术好坏的定论,应依了解艺术的人多寡而决断,如多数人懂的,多数人说好的,便是好艺术;多数人不懂的,多数人说不好的,便是坏艺术。”这种论调未免失平。如果是这样,艺术家将变为多数人的奴隶,而消失其性格与情绪之表现。克鲁泡特金批评托氏这种言论,而谓其过于偏见。盖了解艺术应有相当的训练,在这种美的教育不普及之下,好的高深的艺术怎能使多数人了解,即托氏书中所称为好的艺术,如米勒之画,我们亦不能说是多数人了解的呵!这种无谓的争执,据我个人的观察,渐渐由西方偷过到东方来了。
但是如果我们透彻的研究一下,事实上并不觉得这种问题变成相反的意思。艺术根本係人类情绪冲动一种向外的表现,完全是为创作而创作,绝不曾想到社会的功用问题上来。如果把艺术家限制在一定模型里,那不独无真正的情绪上之表现,而艺术将流于不可收拾。
由作家这一方面的解释,我们就同时想到其他方面的影响,因为艺术家产生了艺术品之后,这艺术品上面所表现的就会影响到社会上来,在社会上发生功用了。由此可见倡艺术为艺术者,是艺术家的言论,“社会的艺术”者,是批评家的言论,两者并不相冲突。
艺术家为情绪冲动而创作,把自己的情绪所感到而传给社会人类。换一句话说:就是研究艺术的人,应负相当的人类情绪上的向上的引导,由此不能不有相当的修养,不能不有一定的观念,我们在过去的艺术史中所得来的经验是什么呢?我们可以说艺术是创造的冲动,而决不是被限制的;艺术是革新的,原始时代附属于宗教之中,后来脱离宗教而变为某种社会的娱乐品。现在的艺术不是国有的,亦不是私有的,是全人类所共有的,愿研究艺术的同志们,应该清楚艺术家伟大的使命。
这是一篇穿过百年历史尘埃依然掷地有声的艺术宣言。重读林风眠先生1927年的这篇短文,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艺术先驱对“艺术何为”的清醒回答,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文化十字路口的理性抉择。其思考之透彻、姿态之独立,对今日被资本与流量裹挟的艺术界,更具灼热的镜鉴意义。
一、历史语境中的破冰价值
文章发表于1927年的中国,正值新文化运动落潮而革命风暴将至的转折期。彼时的艺术界,一面是封建残余的“文以载道”幽灵不散,一面是激进知识分子要求艺术成为革命号角。林风眠却在左右夹击中开辟出第三条路——既拒绝让艺术沦为“多数人”的庸俗附庸,又警惕其蜕变成小圈子的孤芳自赏。他敏锐捕捉到西方“为艺术而艺术”与“为社会而艺术”的争论正在东方重演,却未停留在简单站队,而是将创作本体论与社会功能论分阶段处理,这种“调和”不是妥协,而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法:艺术的纯粹性恰恰是其社会影响力的前提。这在当时非左即右的舆论场中,堪称空谷足音。
二、“情绪冲动”论的当代性
林风眠将艺术本质定义为“人类情绪冲动一种向外的表现”,这一看似浪漫主义的说法,实则暗含现代性锋芒。他所谓“情绪”并非私人化的多愁善感,而是指向一种未被规训的生命本真状态。当他说“为创作而创作”时,实质是在捍卫艺术家对抗任何外部模型(无论是政治教条、市场偏好还是大众趣味)的权利。这种“冲动论”比同期许多理论家更彻底——它不依赖任何宏大叙事的合法性,只承认创作者内在真实感受的权威性。这在1927年需要勇气,在2024年则更具现实意义:当算法能精准预测并制造“情绪”,当AI可以批量生产“感动”,重申艺术源于不可复制的、真实的人的冲动,恰是对技术异化的抵抗。
三、精英立场与启蒙责任的张力
文中对托尔斯泰的批评,透露出林风眠清晰的精英意识。他认为艺术需要“相当的训练”方能理解,这并非傲慢,而是对艺术专业性的坚守。但可贵的是,他未将精英立场固化——艺术家的使命是“负相当的人类情绪上的向上的引导”。这里的“向上”二字极为关键,它意味着艺术不向下迎合,而是牵引与提升大众审美。这种“启蒙”不同于自上而下的说教,而是通过作品本身的力量实现。然而,这一理想在实践中有其脆弱性:如何确保精英的“向上”标准不沦为僵化的学院派?谁来定义“向上”的方向?林风眠未能充分展开,却为后人埋下思辨的种子。
四、对当代的尖锐启示
今日重读此文,感触最深的是他对“多数人暴政”的预警在数字时代空前应验。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、短视频的完播率、艺术展的“出片率”,不正是托尔斯泰“以多数人懂不懂定好坏”的变体?算法加持下的“多数人”比百年前更具暴力性,它制造的不是真正的理解,而是数据的假象。林风眠所言“艺术家将变为多数人的奴隶”已成现实——无数创作者为流量扭曲表达,为粉丝固化风格,艺术个性在“数据反馈”中不断自我消音。
另一方面,他批判的“无谓的争执”也在以新形式复活:当代艺术的“为艺术而艺术”常沦为小圈子的话语游戏,而“社会参与式艺术”又可能异化为道德表演。林风眠的“调和论”提醒我们:真正的艺术自由,从不在乎站队,而在于创作时能否彻底忠诚于内心冲动;真正的社会责任,也从不靠口号,而在于作品能否在问世后照亮他人的精神困境。
我认为林风眠的理论存在一个可拓展的空间:他虽强调艺术的“全人类”属性,却未充分讨论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审美权力关系。在全球化与后殖民语境下,“情绪冲动”是否可能被特定文化霸权定义?中国艺术家的独特表达如何既保持纯粹性,又不陷入“自我东方化”的陷阱?这是林风眠时代未能遭遇的问题,却是我们继承其精神时必须回应的挑战。
此外,他对“艺术品自然发生社会影响”的乐观,也需要审慎对待。在信息茧房与娱乐至死的时代,严肃艺术的影响力日益边缘化,完全被动的“等待被看见”或许已不足够。艺术家的“使命”或许还应包括主动寻找与时代对话的方式——不是妥协,而是创造新的连接可能。
林风眠的这篇文章,其价值不在于给出了终极答案,而在于确立了一个根本立场:艺术的价值尺度,永远在创作时置于艺术家内心,在完成后交予时间与世界。 在百年后的今天,当艺术被资本、技术、民粹三重力量拉扯得支离破碎时,重读此文如同一次精神校准。它提醒我们,无论外界如何喧嚣,艺术家唯一要做的,是守护那份不可复制的、向外的情绪冲动,并让这冲动承载“向上”的尊严。这或许就是林风眠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——以独立之精神,调和自由与责任,在创作中完成对人性可能性的守护与拓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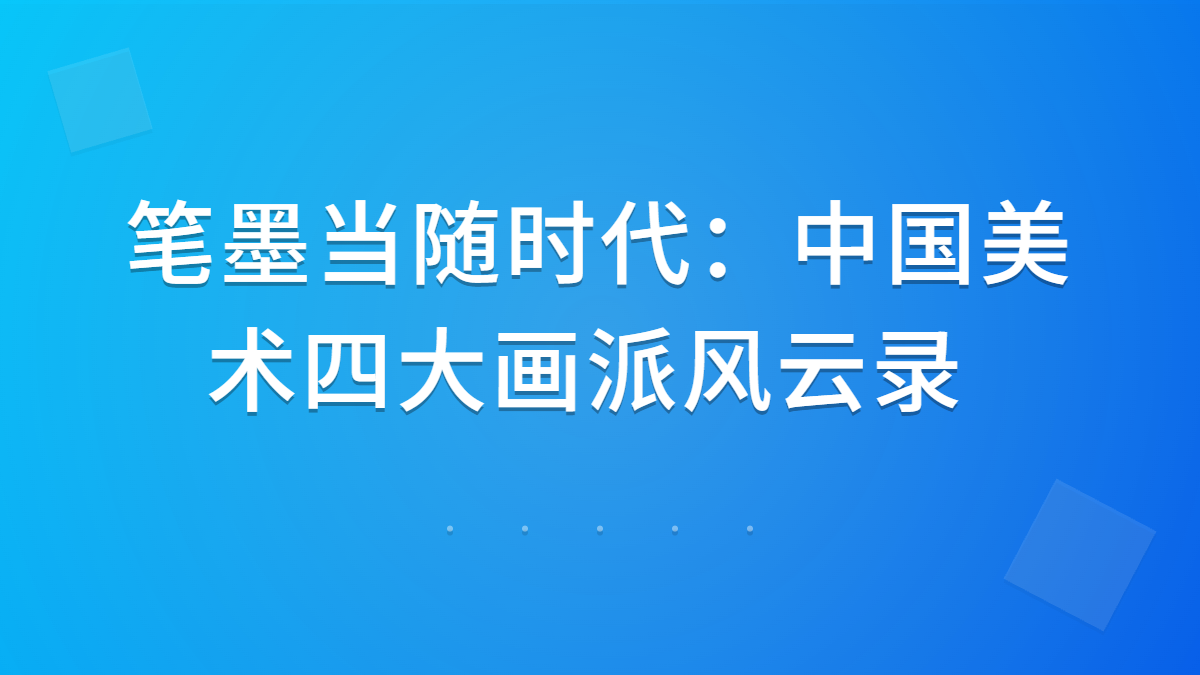

文章有(0)条网友点评